专访刘连香:探讨墓志材料在北魏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编者按】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最新成果——《魏书》修订本于今年元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再次引发学界对北魏史的关注。学者们虽对《魏书》这部“秽史”褒贬不一,但同时又感慨北魏史料的极度匮乏。近年来,墓志材料的大量涌现,对于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这些“层出不穷”的墓志材料如何应用于传统史学的研究?它们对北魏史的研究到底价值几何?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的刘连香老师,请她为我们讲述北魏墓志背后的故事。
刘连香,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石刻学。

刘连香
澎湃新闻:您的学科背景是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为什么后来的研究方向为石刻学?
刘连香:这要从我最初的工作单位说起。我本科毕业之后就职于洛阳古代艺术馆,即洛阳关林,该馆的文物收藏只有石刻,所以最初只能被迫以馆藏石刻为基础进行研究。然而我对石刻日久生情,石刻便成为自己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澎湃新闻:为什么关林这座明神宗时期修建的“关帝庙”竟会有如此丰富的古代石刻遗珍?
刘连香:关林的石刻来源比较复杂,它的前身是洛阳博物馆的一部分,其石刻来源主要包括三方面:1958年洛阳博物馆成立时,洛阳文教局将其原来收藏的一些石刻,包括存古阁的旧藏移交给洛阳博物馆;当时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也移交了一部分;此外,洛阳孟津的著名石刻收藏家、曾编著过《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的郭玉堂先生捐献了一部分。

洛阳关林
其中存古阁的藏石可以说是一部洛阳当地的石刻收藏史,它的建造者是清代道光年间的洛阳令马恕,原址在今洛阳市林业学校院内。据马恕所写的《存古阁记》记载,他广收石刻拓本,“自晋至宋,计得一千三百余种”,一直到民国年间存古阁的收藏陆续还在增加,后来存古阁成为民国时期官办的地方石刻保存所,但在那个年代疏于管理,存古阁只能由旁边千祥庵中的和尚来看管。
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曾于正大七年(1918年)和十年先后两次前往洛阳访察存古阁,据他们所著的《支那佛教史迹》记载,当时存古阁藏石为89石。
1944年洛阳城被日寇占领,日寇投降后由国民党部队接管。因战乱,馆中石刻散乱堆放于院内和走廊。1948年4月洛阳解放,冬天在存古阁成立河洛图书馆,石刻被集中存放。1955年春,洛阳专区文物工作组派员将该批石刻全部运到周公庙北边河南省第二文物工作队仓库院(现洛阳市文物管理局西工分局)收存。到了1959年,洛阳博物馆在王城公园内涧河北岸筹建“墓志长廊”,展出洛阳保存、收集的约千方墓志、石刻,其中也包括存古阁的藏石。当时展品中墓志已达680件。
1981年,洛阳博物馆一分为三,即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和洛阳古代艺术馆,原来属于洛阳博物馆的石刻就保留在了洛阳古代艺术馆,即关林庙。2007年,洛阳博物馆新馆开放时,关林的石刻文物又重新调拨给了洛阳博物馆进行展出。
在存古阁的一批藏石中,著名的有西晋骠骑将军韩寿墓表,韩寿就是因“偷香”而传为佳话的那位公子哥。

西晋骠骑将军韩寿墓表
澎湃新闻:相较于地面石刻,墓志的出现很晚,即便是西晋时期的墓志数量也不多。但到了北朝时期,墓志大量涌现,这种变化形成原因是什么?由碑到志,是什么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刘连香:关于墓志起源的讨论有很多,主要有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等,但研究墓志起源应考虑两方面成因,首先是墓志形制,其次是墓志的文体。就两者来说,墓志都应由地面墓碑转变而成。
东汉树碑厚葬盛行,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于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均发布禁碑令。曹操曾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在他临终之际,还作《终制》:“因高为陵,不封不树。”他提倡薄葬的举措被他的子孙,如曹丕所继承,且一直到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司马炎下禁碑令:“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此外,《晋书·宣帝纪》中还记载了司马懿自己作的《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这种自上而下的薄葬风气对墓前树碑之风打击巨大,但人们想出了折中的办法,将墓碑缩小树立于墓内,取代地面立碑的传统。我们看到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小型墓碑高仅半米,大都还带底座,类似于祖先牌位,碑首形状分螭首、圭首、圜首、方首几种,基本就是借用了碑的原形,只是把它缩小而已。

西晋菅洛墓碑(左)、西晋徐美人墓志(中)与后秦吕他墓表拓本(右)
关于墓志的文体,汉代出土了一些墓砖,比如著名的洛阳东汉刑徒墓砖,它们的文字较为简单,仅仅是交代了志主的身份和卒葬时地等基本信息,因墓主身份特殊,均为刑徒,墓砖的作用仅是记事和标识墓地。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墓砖视为墓志的雏形。
墓志的书写传统应当源于东汉时期流行的墓碑,如《北海相景君碑》,它不仅记载了墓主的姓名、职官和卒葬信息,还包括对其生平事迹和功业德行进行的介绍和赞美,而且树碑颂德在当时成为丧葬礼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的学者还提出买地券对墓志形成的推动作用,但它的内容与墓志存在较大差异,其主要功用是为死者在阴间买地,以达到“生死两隔”的目的,不过它的形制可能会对墓志产生一定影响。
北魏时期墓志出土较多,主要是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呈同心扇面形向北半面辐射分布,距离洛阳越远,出土的墓志就越少,甚至旧都平城的墓志都很少见。这一分布特点显示墓志的使用并非由汉人士族直接承继汉晋墓碑传统,而是由以孝文帝为首的北魏统治集团将汉代墓碑制与魏晋禁碑令进行折中后,创造了随葬墓志的丧葬制度,并自上而下推行使用的结果。
澎湃新闻:早期的墓志形态是什么样的?墓志在墓葬中有没有固定的摆放位置?
刘连香:西晋十六国时,将墓碑缩小埋入地下,在墓室内仍然像在地面一样保留树立形式。东晋南迁,部分墓葬有随葬墓志,但没有形成固定形制。到北魏迁洛,墓志大量出现,并形成方形墓志与盝顶墓志盖一合配置的固定形制,在墓内也由树立变为平置,墓志盖放在墓志之上。一般墓志盖上是墓主人的最重要信息,相当于碑首功能,后来部分墓志盖不带文字,仅起到保护志石的作用。

北魏元显儁墓志及志盖拓本
一般情况下墓志在墓葬中有如下几种摆放位置:一是甬道靠近墓门的位置,二是墓门内侧,三是墓主人头部或脚部。如果是夫妻合葬墓,通常都是在夫妇的脚头位置各放一方墓志。不过也有其他特殊情况,例如北魏吕达(通)墓,在后甬道和墓室之中各放置一方墓志。
墓志形制在北魏形成之后,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后来的墓志一般都是方形墓志与盝顶墓志盖组成一合的固定形式。
澎湃新闻:为什么鲜卑人会采用汉人墓志的这种传统?是否与孝文帝的汉化有关?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北魏墓志在数量上和书写体例上有无差异?
刘连香:北魏使用墓志是孝文帝迁洛之后汉化的重要体现。北魏汉化的时间很早,据《魏书》记载,早在拓跋鲜卑始祖拓跋力微定都盛乐时,就与中原王朝和亲,曹魏景元二年(261年)遣子沙漠汗留魏都洛阳观风土。之后与中原的接触逐渐增多,孝文帝主要受到其汉人祖母文明太后的影响,从小接受汉文化,其迁都后的汉化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
据我统计,截止2015年底之前发现的北魏墓志共532方,仅洛阳地区出土达392方,占到北魏墓志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平城地区仅有19方。在所有北魏墓志中仅有13方刻于迁洛之前,还主要是砖志,内容简略,而且墓主不见拓跋鲜卑,基本是从东、西、南三方归附北魏的汉人及受汉文化影响的其他少数民族。北魏迁洛后,孝文帝下诏南迁之人不得北还,平城的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出土的墓志很少。说明墓志的使用主要是在孝文帝迁都之后。
不同时期出土墓志数量也存在着差异:孝文、宣武时期社会稳定,人口自然死亡率比较正常,墓志的使用数量偏少。随后的孝明帝时期虽然绝大部分人口仍属正常死亡,但墓志的使用比之前明显增加,尤其改葬和迁葬使用墓志,说明墓志已经成为丧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迁都仅仅四十年即走向分裂,到了北魏灭亡前的六年,因尔朱乱政和频繁皇位更迭,造成大量人口集体死亡,以河阴之难、诛杀诸杨最为典型,其墓志数量急剧上升,比之前正常年份超出数倍,死者年龄却普遍偏低。
从墓志绝对数量来看,当时墓志的随葬应该具有严格限制。河阴之难中罹难的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大部分位高权重,目前发现死于此祸的墓主墓志不足2%;尔朱氏在华阴和洛阳诛杀弘农杨氏,百口之家几乎灭门,其家族墓地出土墓志显示遭罹而同日归葬者11人。这两组数字对比,显示出虽然当时被害人的身份地位很高,但却未必都有随葬墓志。
澎湃新闻:从目前出土的北魏墓志中能否知晓当时洛阳地区的葬区情况?孝文帝“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时有没有一个与此配套的葬区规划?
刘连香:北魏迁洛之后,孝文帝下诏令南迁之人不得北葬,但墓葬的规划不是一蹴而就的,北魏刚刚迁洛时并没有一个相当具体的规划,反而显得有点仓促。从迁洛之初最早埋葬的后族冯熙、冯诞父子墓志来看,他们被葬在洛阳偃师的乾脯山,但此地位于曹魏陵区和西晋陵区的夹缝中,地方促狭,不可能再建帝陵。且当时洛阳东汉、曹魏和西晋的帝陵区已经占据了邙山的中段和东段,所以北魏陵墓区只能向北邙山的西段发展。
目前能够基本确定的北魏帝陵有五座,分别是:第一代孝文帝长陵,第二代孝文之子宣武帝景陵,孝文帝六弟彭城王元协第三子元子攸孝庄帝静陵,孝文帝四弟广陵惠王元羽子前废帝元恭即节闵帝陵。第三代为孝文帝之孙、宣武帝子孝明帝定陵。

北魏宣武帝景陵
这五座帝陵以孝文帝长陵最早,也是北魏帝陵的核心,位于瀍河西岸。第二代均为孝文帝子侄辈,为同祖兄弟三人,亦位于瀍河以西,在长陵南面。三座陵墓以宣武帝景陵规模最大,距离长陵最近。节闵帝陵位于景陵西南,静陵则在节闵帝陵再偏南,距离景陵稍远。孝文帝之孙孝明帝定陵位于瀍河以东,距离长陵较远。
从以上三代五陵相对位置看,长陵与景陵、静陵、节闵帝陵均位于瀍河以西,相对集中,应该属于一处陵区,孝明帝定陵则位于瀍河以东偏南较远,中间相隔大量陪葬墓,与长陵已经不属于一个陵区。但以辈分排列,长陵为魏室迁洛后之祖陵,其子侄辈景陵等位于长陵右位,孙辈定陵却处于左位,与昭穆之制方位相反,这说明北魏的汉化并不彻底。在长陵区附近的陪葬墓包括皇室成员、文武百官等,由其与帝陵的位置关系就可以确定亲疏远近和地位高低。这些陪葬墓基本采用家族墓地集中埋葬的方式,这是典型的汉人墓葬排列方式。
除了北邙长陵及其陪葬墓区之外,在洛阳周边还有几处北魏墓区,从墓志记载可知,汉魏洛阳城的东北、东面的首阳山和乾脯山墓区比较大,沿用时间也较长。此外,汉魏洛阳城东南的偃师缑氏一带、洛河两岸与伊阙,甚至黄河以北的河阳城(即今天的洛阳吉利区)也都发现了北魏墓葬。
北魏孝明帝时曾下诏“制乾脯山以西,拟为九原”。但以上这些分散的北魏墓葬都在划定的“九原”之外,反映当时墓葬分布的复杂性。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基本收集了2015年以前所能找到的北魏墓志,就这些墓志所提供的文本信息来看,它们有没有改变人们对《魏书》的认识?
刘连香:不能说改变,而是丰富,墓志作为墓主生平记录,虽说有夸大溢美之辞,但其为当时人撰写刊刻,其中有些信息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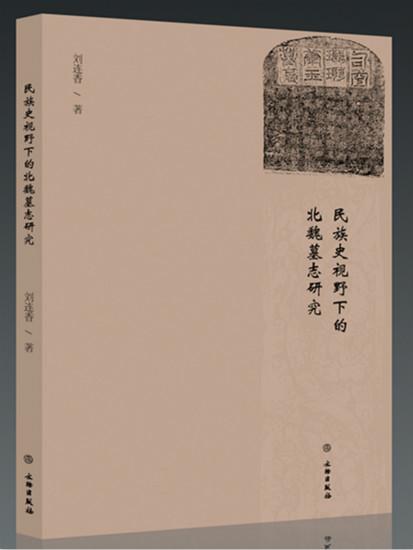
刘连香著《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
以墓志中所记载墓主人不同籍贯地名中较多“都乡”来说,可知北魏后期对于地方的行政管理并非如正史所载的严格实行“三长制”,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平城附近地区实行“三长制”,而在司州附近,即原来汉文化核心区域,以洛阳为例,仍然沿用汉晋以来的乡里组织。
从大量墓志材料可证,当时洛阳城内及东、南、西三面的里坊均属于都乡,说明都乡在北魏时仍为城内首乡,并从行政上对各里进行管理。迁都洛阳之后,对洛阳城中的乡里制进行改革,强化里正、里尉等治安保卫功能,与城市之外的村庄聚落乡里明显不同,最终形成以“里”为实际居住地点单位和以“乡”为行政管理体系的特殊乡里制,同时县令、六部尉直接参与了国都基层管理。北魏时期城内乡里制的典型特征是国都和县城都归属都乡。北魏洛阳城乡里制的强化,实际上是孝文帝推行汉化在政治上的重要体现。北魏继续沿用汉晋以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乡里制,体现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对汉文化的吸收。
但墓志是一种纪实和颂美兼具的文体,北魏时期能够使用墓志的人在墓葬中仅占少数,其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统治集团中的部分现象,并不能体现北魏整个社会结构,尤其无法看到底层百姓的生存面貌。因此,墓志材料仅能反映北魏上层社会的一些特点,这是它的局限性。
澎湃新闻:国内的一些学者曾编有大量墓志汇编,所收材料虽不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但由于收录了大量散落于民间的珍贵墓志,依旧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这些墓志是带有“原罪”的,作为学者,面对一方方因盗掘失去诸多信息、却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墓志,到底用还是不用?
刘连香:文物被盗是当下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持续升温的古玩热加重了这种趋势,不得不说一方墓志如果脱离了它原有的背景,很多信息就丧失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为地把墓志与墓葬中的其他随葬品、墓葬形制等都割裂开来,墓志与墓葬的价值将大大降低。
以北魏的吕达墓为例,这个墓是经过正规考古发掘的,墓中出土了两方墓志——吕达和吕通墓志,一方放置于墓室东南角,一方放置在甬道之中,经过细读墓志可知,吕达和吕通实际上是一个人,之所以放置两方墓志,是因为墓主葬后一段时间又得到了朝廷的追封,比生前的官职要高,可是追封的时候吕通已经下葬了,其家人为了彰显皇恩,又为其刻了一方新志放置于甬道之中。如果该墓葬不是经过考古发掘,仅看墓志还以为吕达和吕通是两个人,又因为两墓志所刻内容基本重复,甚至会以为有一方墓志是伪刻。所以,我们不能单就墓志而看墓志,它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以及组合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不能割裂来看。
我们之所以痛恨盗墓,是因为他们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破坏了墓葬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使原有的组合关系被打破,墓志本身的价值也大大下降。
墓志汇编之类的书籍,也是一些学者为了这些很可能散佚的墓志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做这些工作要付出很大的艰辛,必须要和文物贩子、收藏家、拓工等人打交道,当然他们大都不会告诉编者墓志的“出土”地点,所以现在很难见到像郭玉堂先生《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那样的著作,因为现代的情况比之民国时期又不一样。
这类墓志汇编往往描述某某墓志出于洛阳孟津或邙山,归于某氏,如果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出土地点,即便墓志上写了葬于何处,却不一定是其真正的墓葬所在地,因为有些墓葬迁葬时可能会将旧墓志一起迁到新墓地。如北魏时期,陇西李氏在洛阳偃师的首阳山有一处家族墓地,且李弼墓志也记载葬于芒首杜镇南预墓东隔一峰方岸上,但是墓志却出土在河北赞皇县西高村,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重要的出土信息,那么就会失去陇西李氏家族墓地变迁的一条关键线索。

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拓本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要使用它们,因为正史的材料有限,墓志往往包含了史书中所没有的内容,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有些甚至可以补史证史,运用这些材料也符合王国维所说“二重证据法”。比如目前所见北魏等级最高、价值最大的文昭皇太后墓志也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但该墓志对于确定孝文帝长陵的位置具有关键作用。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