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亚:一个民间故事的传奇

在老家,钓了两天,连鱼的鬼影子都没看见,猴子决定换个地方,于是驱车四五个小时,要去传说中的包二姐家那里去玩路亚。我在东摇西晃中睡了几觉,车轮转了数不清的圈,山路像一条蜿蜒的蛇在山间铺展开来。途中我建议直接去大理,此时洱海边的红杉颜色正是红艳之时,蔚蓝的天空,湛蓝的海水,有红色的杉树,黄色的垂柳,还有西伯利海鸥,晨起的雾轻笼着海面,海面的水汽氤氲着升腾,与雾相接,又形成了新的雾,彼此相溶生长,一幅初冬的和谐样。可惜,握方向盘的不是我。我被拐到了猴子口中的地方。路上,左边的山穷凶极恶,还有落石滚下来,右边是雅砻江,没有汹涌的波涛,平静得很像一块玉碧,绿汪汪的水像被凝固住了。终于,在一个湾了368度的转圈之后,看见一家农舍,说到了,可房子离路边还有一大截,它坐落在江岸边,向下是一段土路,很窄,湾大,75度斜坡,路面车轮碾过的痕迹,像被抹过一层猪油,亮光光的,我担心车轮打滑,一不小心,要么侧翻,要么直接冲下江边去游泳♀️了。我想说要下来自己走路下去,但又显得不厚道,于是我双手拽住安全带,头伸出去帮看路,装模作样的指挥着,一段十米的路程,活活被煎熬成了几千米。不知过了好久,车还是停在了包二姐家门前了。
惊魂未定,打开车门,双脚刚落地,好家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突然像我扑来,双脚扒在我身上,龇牙咧嘴,那条粉红的舌头很是刺眼,妈呀,差点被吓晕过去。岸边一个钓鱼的说:打它,狠狠地打它,说得我好像有降龙十八掌傍身一样,我赤手空拳,拿什么打?但是,我一脚踢出去,转了个身,逃跑开来,那死狗,欺负我矮小,又匍匐过来,我抄起墙边的锅铲,抡圆了打圈,此时:我想起了:哼哼哈哈,快使用双截棍。果然,有武器在手,那狗只得瞪着眼睛,讪讪地走开了。其实,那狗是不咬人的,只是有点人来疯,不然,我早就皮开肉绽了,哪还有我唱双截棍的份儿!
这里,只有一户人家,钓友们唤女的为包二姐,她身材略嫌肥胖,脸色红润,头发花白,爱说话,话语间总是显露出她的豪爽与幽默。男人似乎受过伤,一块布袋挂住一只手,一顿饭,就两句话:嗯,哦。就没再说过。三个先到的钓友,在一桌吃饭,一个有六七十岁左右,和包二姐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上一句与下句八杆子打不着,但他们又总能一直说下去。另一个,皮肤白皙,鸭舌帽下驾着方方的眼睛,话不多,吃饭间,总习惯性地用手凑一下眼睛,似乎不小心,那镜框会落在碗里似的。还有一个,脸上长有大大小小的豆豆,似乎又不是,应该是肉疙瘩,不规则的,一颗颗堆挤在脸上,显得特别精神,于是,我想起了课文中描写列夫·托尔斯泰的皮肤:“小屋粗制滥造,出自一个农村木匠之手,倒像是用刀胡乱劈成的树柴。皮肤藏污纳垢,缺少光泽,就像用枝条扎成的村舍外墙那样粗糙”。他话很多,一顿饭间,他讲起了他四十年前的一段爱情。爱情的模样总是让人动情,无论发生在怎样的年龄。一辈子,总要有一段情,在这样的夜晚被讲起。
夜色下的山,黑压压的,像厚重的屏障,那刀削般的悬崖拔地而起,危峰兀立,令人望而生畏。远远地望去,那悬崖是那么高,那么陡,好像是被人用巨斧劈峭过似的。对面半山山腰上闪耀着几盏灯火,空中的一轮半月怎么也照不亮山间浓重的夜色,几颗星星闪烁,倒是明亮。不知名的小虫叽叽喳喳,窸窸窣窣的声音就没停过,水中的鱼儿跃出水面,任凭垂钓的人把鱼竿摔得刷刷作响,鱼就是不上钩,天气冷了,鱼也高冷起来了[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社会社会]。我选了二楼的房间,披着外套,坐在阳台上,听着小虫的鸣叫,虽看不见跳跃的鱼儿,但它一定也想冒出水面,看看,是谁?那么执着,想钓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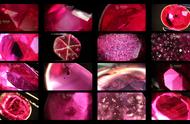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