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里满:我成长的地方

故里人文初探(之一)
何同桂
图片 / 饶阳微发布

( 何同桂,一九五二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饶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人大副主任、作协主席和衡水市作协副主席、孙犁研究会副会长、诗词协会理事等。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出版诗集《案牍余韵》《土屋杂咏》,小说集《芝麻花》,散文集《榆钱的回味》《土味人生》,记实文学《孙犁在饶阳》等。)
文友邀写故里,这是大题目,只能大题小作。
我家是饶阳东里满村(和西里满对应)。“里”是古代社会计量单位。秦末十户一“里”,汉初百户一“里”,十“里”一亭。刘邦原为亭长,治管千户,也算人物,无怪吕公主动嫁女。至明沿用汉法,“满”者其意自明。
东里满建于何时无考。流行说法多为洪洞移民所建,我有怀疑。饶阳建县两千多年,当时须具人口规模。滹沱水灾频仍,百姓择高而栖。里满一带至今是饶境海拔最高点,唐时县治所曾移固店,里满更应是繁庶之地。据我推测,“里满”是秦汉己“满”,或唐宋已“满”,非明初移民填“满”
东里满村,何姓十之八九。其它张王李刘魏靳孙马等皆为小户。我家那个俗称“牌坊下”的生产队,除一张姓外,皆为何姓。
里满何姓始于移民也有待商榷。至今兄弟三分之说流传甚广,饶阳何姓一致认同:老大“碾何”,在东里满;老二“磨何”,在大何庄;老三“碓何”,在影林。“碾磨碓”皆粮食加工器具,可见饱腹之难。吃饭家伙,竟成图腾。如按移民说,是在洪洞分家,还是到哪村分家?我想何姓原系饶阳土著可能更大。这样无论在哪分家都情通理顺。何姓为中国十九大姓,全国分布较广,以南方居多。
移民之中即使有何姓,也不排除里满居民中原有何氏先人。村中久有东何西何之说,也不明就里。而影林何庄则无此说法。

东里满人文特点之一
重学崇文
本村史无高官,难称人杰地灵,但重学崇文之风却源远流长。
村西头有座牌坊,百里闻名,高大巍峨,是为监生何榕之妻戴氏守节教子所建,由乾隆帝颁旨修建。国子监相当教育部和大学的联合机构,乾隆帝年授一课,监生在院里跪伏听训,传讲官大声复述皇帝每句“金口玉言”。我参观过国子监,临境顿生肃穆之感。何榕英年早逝,未任官职,但学名远播,所以清帝彰其遗孀。牌坊由石条砌成,工艺精湛,宏伟美观,三层楼高,三拱出入,石狮威武,图案华丽。石条雕刻花卉、鸟兽、云锦、松鹤等图案,还有“古井铭心”、“为人旌表”、“筠松比品”、“课子丸熊”等铭文铭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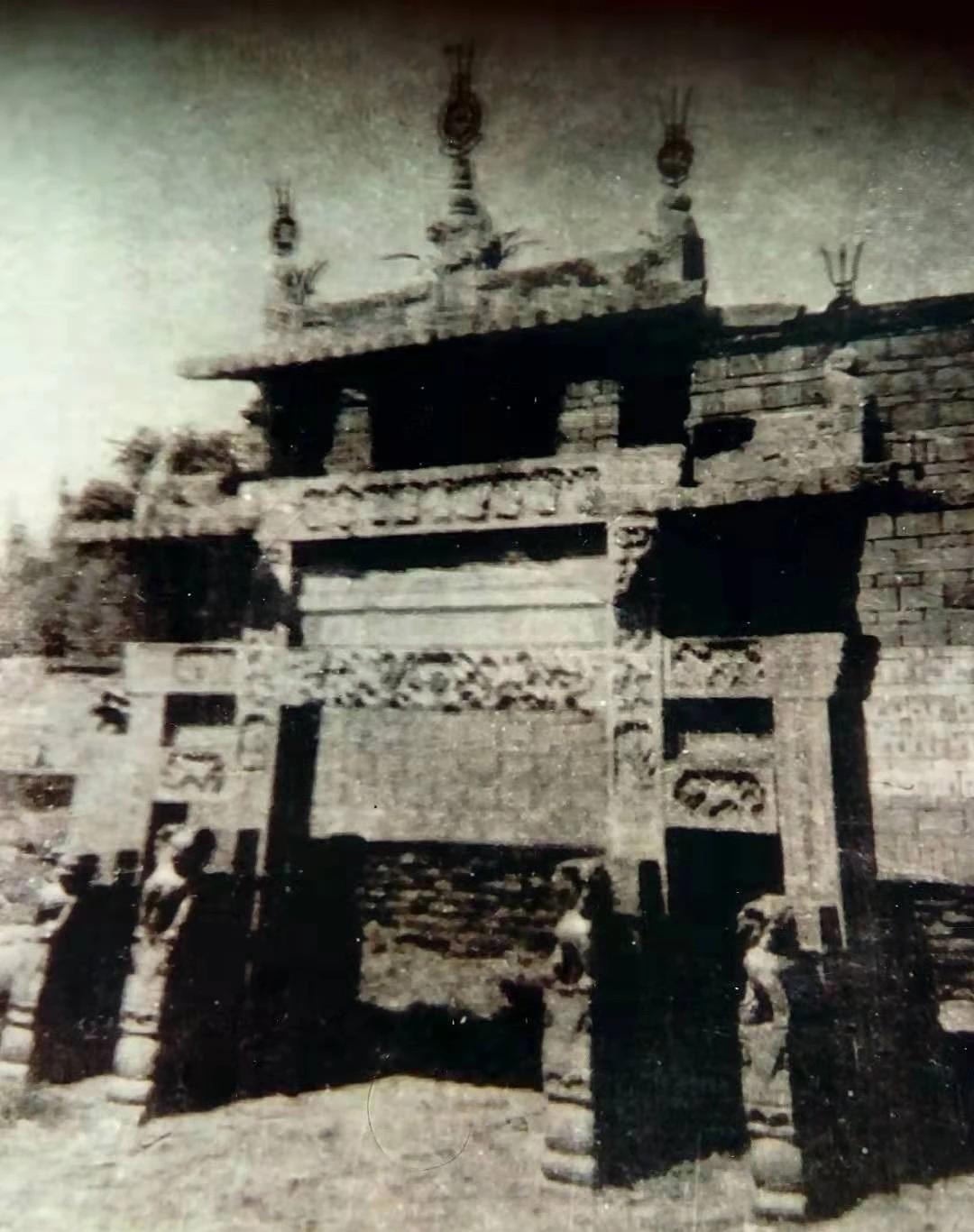
牌坊下人皆以求学上进为荣。民国县志载在外求学人数不多,我村何姓二人在列。一名何丙章,一名何同章。何丙章抗战前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时已有子,他的爷颇为自豪,诗记“四大喜事”:“上大学,开酒铺。重孙子,大杨树。”诸多喜事把上大学排首位,价值观令人慨叹。他家过去富裕,种地同时尚有买卖。那片杨树我小时还在,不过二十来棵,但茁壮伟岸。
我队唯一张姓人家,老人教过私塾,人皆尊称“张先生”,常找我家对门的宝清爷“讲古”。宝清家原是富户,也有文化,爱讲《聊斋》故事。张先生却常说《今古奇观》。夏季纳凉听故事乃人生至乐,现在再无此享受之事。恢复高考后,张先生的孙辈好几个考取大学。我曾写《乡村先生》一文,把他比做《白鹿原》中的智者朱先生。

同学书垛的老爷爷是名秀才。他父亲也精书法,擅丹青,每年自书对联,描绘花灯,有时还在雄鸡喜鹊图上题写诗句。我爱找书垛,每见他作画即看得入神。那时求学无门,借书也难,常感惆怅无助,母亲常说:“去找大垛玩儿吧。”我去串门,他父亲也总说“就你来他高兴”。
何瑞生也是牌坊下名动四乡的才子。他长我十岁,上过初中,跟过剧团,能写会画,能拉会唱,研读古籍,也写诗文,还学过医。他家常有几个村野文人谈书论艺,逗闹调侃。及至老境,他说:“我的天分是画画和拉弦。”他操琴小有名声,业内人称“南霸天”(滹沱河南最好的意思)山水画参加过国家层面的展览,离世前已被省会某画廊包销。我上农中时常去他家,借过四大名著和一部《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书中例举的那些诗词都抄过,至今尚有印象。他诗文也好。记得一首《咏蝉》诗“居在丛林里,乐时起细吟。不须思远举,受露满清心。”他念后和我说:“还要请教一下张先生,看合不合平仄。”这是我首知“平仄”之论,不过至今未通。后来我赠瑞生一诗,内有“文史哲医皆成趣,诗书琴画触类通”“自古奇才雄伟士,多在乡野布衣中”。诗不合律,意却真诚。四乡八里似瑞生之才,几十年尚未见。

村人重学。前些年每有人考上中学和大学,村人皆奔走相告。一九六五年饶中高考考生不到百名,我村却有三个。除一名政审原因,两名都被名校录取。落榜之人也找到理想工作,我辈羡慕至极。我在县城虽无权柄,人头也熟。乡邻相托,多为求学。为上高中职中,很多人家节衣缩食,令人感动。
搞文字的人多,也是东里满一个特点。文字工作含辛茹苦,无名无利,但我村曾长期从事的人很多,计有何彦君、何卫、何航平、张建发、魏跃立、李方讯、王恩厚等人。据我统计,可谓全县之冠。这些人为官低调,默默无闻。即使后任其它职务,还是不失文人本色。魏跃立从县委秘书调公安系统任110指挥中心主任,多年矢志词曲创作,谱写几十首新歌。《公安干警之歌》唱响全省,《饶阳之歌》家喻户晓。春节期间他把软件给我一放,真令人眼界大开。我说:“你给故城、北善旺都写了村歌,该给咱村写一首。”他:“你出词吧。”这词自然不好写,但无论怎样写,也要有“文脉”二字吧。
文脉不是煤矿。文脉是一条若有若无若隐若显的传承之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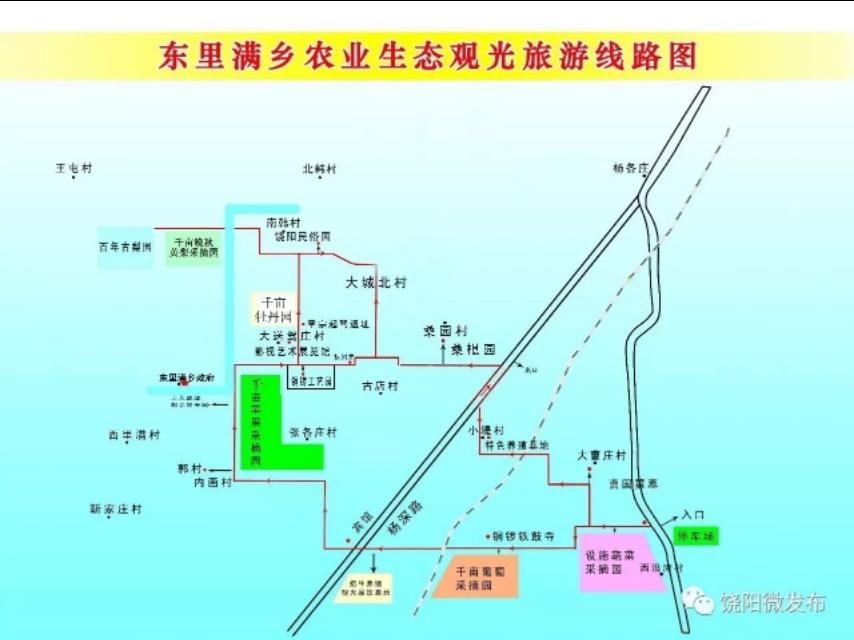
东里满人文特点之二
重迁安土
汉书上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安于本土,人之常情,东里满人尤甚。
举个极端的例子。民国时期,名声最著的人物是何世荣,又名宝泉,是我家对门宝清爷的哥哥。他多年任四区保卫团长,手下人枪过百,出入马弁蜂拥。既有作威作福之迹,也尽保境安民之责。深州巨匪徐二黑绑票杀人,为祸百里,但惧何世荣之威,不敢轻易骚扰饶境。有次徐匪趁夜到五公一带抢劫,提前被何侦知,率队埋于沿湾,把徐匪打得落花流水。日寇进占华北,徐二黑即成汉奸,何世荣却毅然参加党的抗日游击军,任四大队队长,号称“何团”,队伍扩至千人,屡有战功。(当时四个大队,著名烈士许佩坚也是大队长,号“许团”)但后来上级命令“何团”进山整训,何世荣称病不走,坚持就地抗日,却被强行用担架抬到某地秘密处决。他的部属,凡活过来的都是离休待遇,他却魂断异乡。

征集党史资料时,我采访过院头村老干部韩培义。韩是建设部副部级干部,曾任“何团”党代表。韩说:“何世荣和我关系好,他听我的话。他不是坏人,就是恋家吧。我要不调回民支队当政委,不会出这种事。”看来人的荣辱沉浮,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有时与何人共处也很重要。
我村读书人多,工作人多,工作人中教师多。而这些教师中,三年困难时主动离职不在少数。据我估算不少于二十。文革后落实政策,有些被打右遣返的得以平反,自动离职却不在“落实”之列。我一发小之父,原在桑园完小任教,威望很高,人缘也好,很受校长器重。因关系密切,校长还把我的发小认成干儿。精减下放时他却主动辞职,校长反复挽留也未改主意。谈到此事,老人曾说:“要不是非走,下放十个也轮不到我。”联想何世荣,即使韩老在旁,也许不听劝谏吧。

故乡人虽重研修学问,但难谈胸怀大志。我常想,莫非是家家平地起房门墙高耸限制了登高望远的眼光?很多学生分配或军转干部都要求越近越好,能回县城则不留省会,甚至能到本乡则不留县城。前几年盛行出国热,也没听说本村优秀学生外出。有两个才女异域发展,也是配合老公事业。

蜗居一隅,甘于现状,于我本性颇合。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北日报》衡水记者站站长蒋清泉调我,县委未准,倒趁我意。一九八三年,地委宣传部肖功柄部长调我工作,我说爱人是职工,在衡不好安排。肖部长说:“咱管着报社,到报社工厂上班。”他看我不坚决,叫王启元劝我,我说:“年龄大点了,算了吧。”王老师是我老领导,不客气地说:“你三十就算大?那就窝里老吧!”现在真老了,倒有点跃跃欲试之心,可惜此生再无机会。

孙犁说:“梦中屡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思乡之情老益浓,东里满人尤突出。近年有多年在外者回村建房,似成新的风景。我原想,他们是学项羽圆“富贵还乡”之梦,还是效陶令享“南山东篱”之趣,甚或二者兼而有之?现在想来还是落叶归根的情愫所致。我老家旧房三间,多年失修,已经塌漏。院落杂草丛生,椿槐疯长,虽破陋如斯,不忍舍弃。读过孙犁《故园的消失》一文,大师曾说:“看着这个院落,人们就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人。”我虽不才,心情与大师相似。孙犁给老屋留下一照,旧房三间,挂一耳房。我原想也拍一张,又觉毫无意义,遂作罢。

东里满人文特点之三
重义轻宦
东里满史无高官,现代也鲜有身居高位者。书香浓郁的古村为何无显赫之人?载入民国志的读书人应属凤毛麟角,两位先辈也是执教终生,甚至难称高知阶层。
究此现象,想到一个近乎演义的人物——“何大疯子”。此公是牌坊一支的先人,自幼攻书论剑,文武兼备,膂力过人,威名远播。据说曾遇疯牛撒野,危及村人,他迎身攥住牛角用力一拧,疯牛即刻倒地。明末嘉靖年间,严嵩当道,权奸横行。武状元大比之期,此公斩关夺隘进入殿试。殿试科目倒也简单,一把百斤大刀只要耍十个刀花,即得钦定状元。很多人虽上下打点,但一看阵势只得知难而退。唯有此公轻而易举运刀如风,令嘉靖连声叫好。他若此时叩头谢恩,状元即成板上钉钉。但他舞得兴起,耍弄百合尚有余力,嘉靖目瞪口呆,严嵩因未受此公之贿,借机奏道:“这是个疯子。”何氏先人本也无意仕途,遂愤然而去。从此传开一个“何大疯子”的故事,引起后人无限遐思。

买官鬻爵,官场通病,于今未绝。“疯子”未通门径,不懂察颜观色,纵有浑身武艺,何谈施展抱负。即使得到封赐也未必平步青云,稍有不慎还可招致祸端。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打“右派”五十五万,我村因知识分子不少,也有几人不幸跌入网内。一本族大伯供职峰峰矿区,反右初始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因屡为蒙冤下属辩解遮护,自己反被打右,全家遣返回乡。文革后县委落实政策,他多次对我说:“当时向上汇报都是我去,虽挨批评咱也不能冤枉好人。后来组长去开一次会,右派名单却把我添上了,这样他们就完成了指标。”
还有一位近邻,是包钢医院名医,医术精湛,性情耿直。因常出逆耳之言,反右时立即挨整,上级未复即强行押回原籍。这位同乡悲愤难抑,当日服药自戕。后上级否决单位意见,未定右派,单位也不告知,致使蒙冤二十余载。落实政策时无档,其子找到包头方明真相。随波逐流者顺风顺水,刚正耿介却遭灭顶之灾,实在令人扼腕。难怪有人问国学大师季羡林敬佩谁,大师果断地说:“当代人最服彭德怀!”

建国前后,邻村颇有几个老幼皆知的政界显要,如西里满金城、大送驾庄宋子珠郭子恒、张各庄李国华等。我村自然也有出类拔莘之材。如抗战初的饶阳县长杜友迈(贺丰)即其一,职务应在曾任四区区委书记李国华之上。他唯一的孙子杜铁林与我同年入学,一直在家务农,直到因意外事故去世。尽管他爷爷的下属或战友不少在省县握有权柄,但没得到一点庇荫和照顾。建国后职务最高的应为何子伦何子力兄弟,一为吉林省军区后勤部长,一为外交部某司司长。虽任要职,但他们都为人低调,自律甚严,从不利用影响给家人谋利。我在省委招待所修改党史稿时,有次省长张曙光听说我是东里满人,还认真地说:“我认识你们村何子力。”县里开党史会,何子伦兄弟都在邀请之列,但他们都没能到会。后来不少老干部借此机会回家探视,县领导对这些前辈非常尊重,有些人也借机提点个人要求,县里自然尽量满足。我在县委政府两办多年,又搞过党史,所以陪同领导接待此事无以计数,但却没接待过本村的老干部。我大伯也是“三八式”干部,抗日时曾在外地任县委书记,进城后也是领导干部,但他回家都坐班车往返。有次班车人满,由我找一马扎挤坐回津。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找找县里,他:“我参加革命在外地,对这里情况不太熟悉。再说咱不能轻易给人添麻烦。”
自律为人,无意为官,偶涉官场也不善弄权,似是东里满人一个特征。

♧
东里满人文特点
之四
重德向善
曾写《大善之县》,述饶阳人文特征。今思故里,略记凡人小事。
从家庭进入社会,我第一个人生导师是登麦爷。
登麦爷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在街面威望极高。从建社到散队一直任队长。队长不算官,但要统筹几百人的生产生活,还要天天带头劳动,费力操心也沒任何补助,所以许多小队班子经常瘫痪。但登麦爷从沒撂过挑子,即使选举也必是滿票。我十三高小毕业,想出工找他要活,他想了半天说:“你这嫩骨嫩肉的,去看花生吧,只能记四分工。”那时整劳力是八分。他儿子玉岗大我两岁,同年毕业,却被派干累活,也记四分工。这是我踏入社会第一步,此事使我铭记终生。
登麦爷古道热肠,纯朴厚道。文革时,国际关系学院两个女教师下放我队监督劳动,登麦爷反复叮嘱人们不要歧视,尽量照顾。队上除安排饮食起居,还总给她们派轻活儿。她们吃商品粮,不应分配。但秋收时登麦爷总派人送去红薯、萝卜和花生,有时还挑嫩玉米叫她们尝鲜,尽管那时人们的口粮并不充足。多年后,我凭记忆写一散文《华克放》(是其中一个下放教师之名)登报后被这个老师的学生看到。该生给她寄去报纸,据说华克放非常激动,说十分感谢里滿乡亲,并叫那个学生到饶阳找我,说记得那个叫登麦的队长,,表示有机会来看望人们,并告我家中电话。但那时登麦爷早已做古。

我参加工作后,常看登麦爷,多次表示对他的敬佩之意。他却说:“我的为人处世,都是跟你爷爷学的。”
我爷爷死于五二年旧历二月二。我是爷爷逝后这个家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虽未谋面,但老人们都说爷爷急公好义,心地善良。爷爷出身贫苦,从小给人过继,始承若干地亩和一所两进宅院。那时村人喜欢闹戏,愁于场地,爷爷就把前院西屋腾出,叫人们排练演唱,至今传为佳话。登麦爷从小父母双亡,爷爷待他视如子弟,不仅帮他修房种地,还叫奶奶缝衣做鞋。及至登麦爷稍大,爷爷看他聪明能干,就常带他参与一些街坊平息纠纷化解矛盾之事。登麦爷后来人情练达,思虑周密,或许与此有关。
厚道宽容,与人为善,也是村风的重要方面。还举我家为例。土改初期有些过“左”,全县有几百户错封错分,我家外院西屋也被拆走木料。后期纠偏,幸留宅院,但在西屋旧址又安放一盘碾子。这样加上原有的磨棚,前院就成乡邻的公用场地。到我十几岁碾磨尚在,每天日夜有人推碾拉磨。而我们和大伯一家十来口人挤住后院,皆无怨言。磨要石匠杵,碾子要撂油,家人也都乐于承担。为给人们提供方便,我家白天从不锁门,以供推碾者歇脚喝水。(院里有水缸水瓢)遇孤寡老人推碾,家长就吆喝我们堂兄弟帮忙。后来我常想,这套院子给乡邻带来诸多好处,但于我家能得到什么呢?于我而言,倒是自小听到不少家长里短的轶闻旧事。
纯朴厚道,怜贫惜弱,是乡邻共性。对门宝清爷地主成分,那时村上常叫他扫街,自然带有强制性。我们小时疯玩,大人就说:“别乱扔砖头瓦块,给你宝清爷找事儿!”
宝清爷去世后,老伴书锦奶奶一人度日,晚景自然有些凄凉。有年除夕中午,她吃饭时不慎滑倒,菜洒碗破,不禁嚎啕大哭。我们一过道人都跑去,纷纷叫她回家过年。她哪都不去,于是人们有的端菜,有的送馍,有的帮換洗衣裤。我的母亲下午陪她半天,直到她破啼为笑。母亲回家后和我说:“你帮着找找乡里,叫你书锦奶奶去敬老院吧,一个人太可怜了。”书锦奶奶进敬老院后,我去看过一次,见她穿的干淨,也胖了。她高兴地说:在这里天天歇着,顿顿都是白面。”

前些年,常讲“阶级斗爭为纲”,但村人似无多少这种意识,倒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根深蒂固。想起两件小事可见一斑。其一、“四清”时组织大会揭发干部,会前为活跃气氛,主持者叫一闹戏老者来段京剧。此老挺身而立,大步上台,亮开嗓子唱道:“不做官来不受害,不吃俸禄不担惊……”戏未唱完,群众鼓掌,主持者听着似不对味儿,遂哄下台。其二、文革中批斗干部,某老人发言声色俱厉,但却“有弹无药”,只扣帽子,却无内容。此时挨斗人突然“唉哟”捂肚喊疼,揭批之人却立即上前抱住他说:“兄弟,给你根烟抽,肚里有点热气就好了。”说着麻利卷好一根“炮筒”塞进对方嘴里。前一事村人皆知,后一事我亲眼所见。
悠悠古村,芸芸众生,自有奸刁顽劣之徒,也不乏卑鄙龌龊之行,但我不想诉诸笔墨。原衡水文联主席李清对我说过:“你能写好人有多好,你看不透坏人有多坏,所以你写不好小说。”
如果写不好,只有一个办法——不写。
好在我不是写小说。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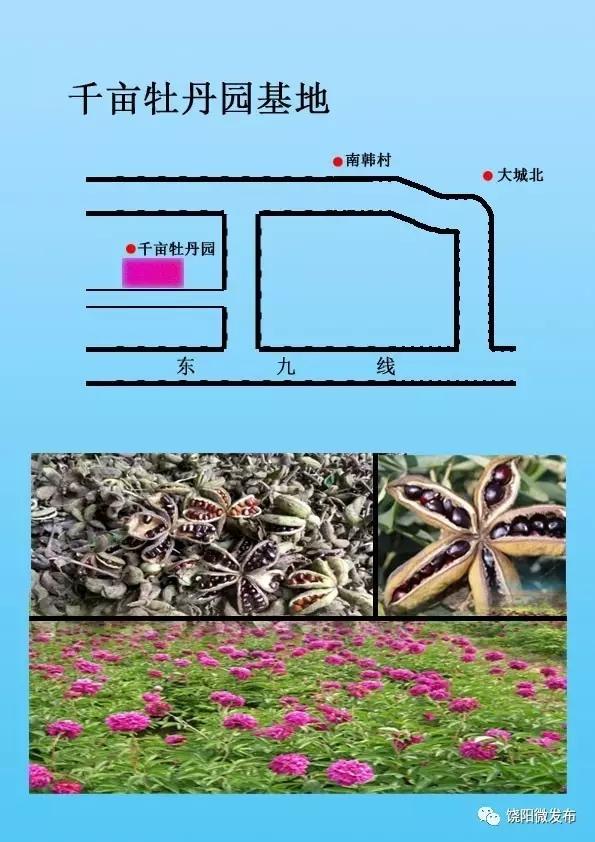
♧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