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贝楼的迷失与寻找

上个月,妻子拉着我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为她选养老院。她说养老院将是她孤独的归宿,我得帮她选,将来要是想起来回来气她,从“那面”找过来的路我就认识了。
二是为我选墓地。她说墓地是我的归宿,入住墓地我就达到目的了,自由了。想抽烟就抽烟,想不吃药就不吃药,还可以熬夜,只要不出来吓人随便熬夜,谁也管不着。
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含蓄地指责我,虽然被确诊为早期肿瘤,却不按时吃药。肿瘤在肺部,医生也颁布了“戒烟令”,我却阳奉阴违,继续偷着抽烟。这些作死的对抗,让她气闷。
妻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很直白,却让我心中怦然而动:她为我讨要了一条纯种的比格犬。

我家的比格
妻子老战友家的比格产崽才两个月,妻子就抱回一只。她说比格犬是猎犬,体力充沛,必须每天遛狗三次。
没有比格时,早中晚各一“吨”的药下肚,直接就饱了,根本没胃口再吃饭。比格来了,早中晚领着它穿街越巷,又会感觉到饿了。饿的感觉真的很好,你也许从来不知道,至少以前我不知道。
妻子了解我:童年时,我曾拥有过一只狗狗,狗狗陪我治好了一场大病,他离开妈妈时,也是两个月大。后来,因为我的一次“不得不”的撒手,狗狗丢了。狗狗应该一直在找我,这样的执念伴我一生。
没有留下照片的小土狗,驻扎在我的生命里,我却写不出它的名字
拥有小狗狗时是1974年,在黑龙江省北安县,我7岁。满世界也没有几台照相机的年代,不可能留下他的照片。甚至连我给他起的名字都是勉强写出来的,他的名字叫贝楼。
见到贝楼时,觉得他额头特别大。额头,东北话里也叫贝儿头、贝儿楼头,于是我叫他贝楼。
贝楼的妈妈赖赖呼呼算军犬,养在部队医院炊事班,但这母子俩却是一点不掺假的土狗。母狗一窝产下六个狗崽,贝楼是唯一抢不上奶的那个。养狗的战士看这样下去不是事,就抱着他到病房外面讨要羊奶。

本图片来自网络
部队医院的番号是351,所有的房子都是平房,养狗战士就隔着窗子向里面的病人要羊奶。在当时,351是北安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没有牛奶供应,吃“半流”的患者的早餐才有奶粉或者羊奶。无论奶粉还是羊奶,炊事班都不经手,由营养部统一分发给半流、全流的患者。
我是因急性黄疸型肝炎住院的,差一点死了,好歹把命保住了,却已经在单人传染病房里关了三个月。住院的第一个月,刚好妈妈产下妹妹。为了妈妈和妹妹的安全,父亲和弟弟都被禁止探视我。每天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见不到其他人。好不容易急性肝炎治好了,黄疸却没退,连眼白、指甲白都是黄的,就像一个香蕉人。香蕉人自然不能离开病房,父亲还是隔好几天才能来看我一次,也只能坐在病房的外面跟我聊天,现在想起来像是家属见囚犯,我就是那个囚犯。
两个战士抱着小贝楼来要羊奶了,他们已经敲了好多病房窗子,却没有要到羊奶。因为吃半流的病人不多,几个吃半流的病人,无论奶粉还是羊奶,早餐时就喝光了,根本留不住。由于羊奶有膻味,我一口不喝,还剩着满满一小盆。忽然觉得这盆羊奶将是我的砝码。
两个战士向我要奶,我却向两个战士要狗,隔着窗子与贝楼对视的一瞬间,似乎心灵相通,认定他就是我的伙伴。
天津兵一口回绝,他说:小屁孩一个,自己能不能活还不知道,还养狗?你敢在病房里养狗,得的是肝炎还是脑炎?
大连兵却说可以把小狗给我养,他对天津兵说:这孩子吃半流,有奶……
就这样,两个战士隔着窗子把贝楼递给我,唯一的条件是我得保证给小狗喝奶,而且出院的时候一定要把小狗送回炊事班。
孤独了整整三个月,终于有了自己的伙伴!接过贝楼的瞬间,只有自己知道有多欣喜。

本图片来自网络
贝楼特别喜欢喝奶,于是,不管是羊奶还是奶粉,我都让护士阿姨打满两碗。护士刚刚离开,贝楼就从隐藏的床下钻出来,呼噜呼噜地喝奶,不到中午,贝楼就把奶给喝光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没有奶的时候,贝楼也会从床底下钻出来,舔着食盆,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半流、全流都是患者的进食方式,半流一天吃五顿饭,基本不吃固体食物,早饭是奶。全流一天吃七次,早晚都有奶。
不能让贝楼饿着,去找医生要求吃“全流”!全流没有固体食物,却有两顿奶,我已经三个月不知道啥叫饿了,不在乎有没有固体食物,只要贝楼吃饱就可以!
医生是大人,三句两句就套出了我隐瞒了三天的秘密——居然在病房里偷偷养狗!这大概是351有史以来的唯一一例。起初医生护士都不信,直到她们亲眼看见了藏在床下的贝楼,看着贝楼惊恐而乖巧地摇着小尾巴,她们才信了。恰好那天老爸来看我,我的“事迹”就被通报给了家长。
老爸是来给我送草药的,为了治我身上的黄疸,爷爷从皖南寄来了两大包柳根,一包泡服一包煮服,一天喝四次,一共是八碗,一次一碗也不能少。
就像换来贝楼的羊奶一样,我又发现了谈判的筹码,就对父亲和医生说:要是不让我养贝楼我就不喝草药。反正你不能每次都看着我,我就把冷服的直接倒掉,热服的放凉后再倒掉,黄疸不退就不退,谁让你们不许我养狗?
两人无奈只得答应,老爹和我约定,要按时喝药,好早点回家。医生也和约法三章:小狗不许出病房;粪便之类要我自己处理干净丢到厕所;小贝楼不许高声吠叫影响他人。违反任何一条,立即把贝楼送回炊事班。同时,医生还嘱咐护士通知营养部,每天给我两输液瓶羊奶。当然,这是给贝楼的。
这位医生我一直记得他,他姓齐,哈尔滨人。

图片来自网络
护家的贝楼连立奇功,成为了全家的朋友
贝楼再也不用躲在床下了,说了你可能不信,开始时,只要有护士的脚步声走近,贝楼就迅速躲到床下,像一个机警的孩子在玩躲猫猫,一点声音都没有。
爷爷的偏方果然有效,几天下来黄疸逐渐消退,终于可以出院了,我都要急死了。有了贝楼作伴,我已经不孤单了,此时着急出院,主要还是因为贝楼。
一天,贝楼妈妈和兄弟们不知道怎么从炊事班那边跑到了病房外,他们的叫声贝楼听到了,他激动地蹭我的腿,冲着窗户奶奶地叫。在此之前贝楼几乎一声不叫,如果不是偶尔听到他冷冷地哼哼,还以为他是哑巴。
等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把他抱到窗台上时,狗妈、狗兄妹早就不见了。贝楼在窗台上蹲了很久,一直望着窗外,又奶奶地叫了几声,似乎有着无尽的失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贝楼养成了习惯,没事就蹭我裤脚,央求我抱他上窗台,在窗台上他会静静地眺望很久。我猜贝楼是想妈妈了,是想出门奔跑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很害怕,害怕贝楼会大叫。大声吠叫是违反约定的,一旦违反约定,贝楼就要被送回炊事班。

本图片来自网络
爷爷神奇的偏方,加上我一丝不苟地执行,终于从香蕉人恢复成了正常人,终于可以回家了。(前文链接《老中医偏方的故事》)
老爸的部队离医院很远,我们住的家属院离医院更远。在家属院,贝楼听不见狗妈妈和兄弟姐妹的叫声了,就不会离开我了。没有按照约定把贝楼送回炊事班,而是带着贝楼窜上老爸的吉普车一溜烟地逃出了医院。
离开医院大门的时候,唯一一次坐吉普车的贝楼,凝望着渐渐被车子扬起的烟尘遮蔽的医院,激动地叫了几声。
当时只担忧如何应付接下来的局面,并没有在意这位伙伴为什么对着烟尘中的医院吠叫。后来,在贝楼的事情上我有过很多后悔,斩断他与自己妈妈的联络,也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

如我所料,老妈不喜欢贝楼,坚决不同意我养他。好说歹说,加上老爸帮腔,老妈勉强同意贝楼留下,却不许进屋,只能睡在院子里,她怕贝楼吃了“脏东西”把屋子也弄脏了。这一点她想多了,贝楼只吃食盆里的东西,食盆就是我最早给他喂羊奶的小盆。食盆以外的东西,必须我亲手喂给他,否则他睬也不睬。
但是,贝楼住在院子里终究不是个事。开始是夏天还好说,转眼两个月过去,马上就要进入十月,北安的十月随时都能下霜。贝楼还不如家里的母鸡和大鹅,鸡窝鹅圈都在门斗里。妈妈无视我的请求,坚决不许贝楼进屋。老爸见我太难过就答应,国庆节放假时抽空在院子里给贝楼修个小狗窝,多少会暖和一些。
还没等到国庆节,妈妈就允许贝楼搬到门斗里了,因为刚刚六个月大的贝楼立下了护家一功。

图片来自网络
一天夜里,门斗里的三只白鹅公主忽然紧张地叫了起来,三只白鹅公主一边叫一边扑棱翅膀,弄出了好大的动静。爸爸连忙出去查看,看见有人来,白鹅公主不咋呼了,老爸却听到院子里有声音,是贝楼在打喷嚏,过去一看惊呆了——
一只黄鼠狼仰面朝天躺在院子里,脖子被咬出了两个窟窿,正蹬着腿倒气儿。显然,黄鼠狼试图穿过院子再钻进门斗偷鸡偷鹅,刚刚经过院子就被贝楼逮个正着,一口咬住了脖子。垂死的黄鼠狼使出保命绝招,放了个恶臭恶臭的屁,贝楼被臭屁熏得不得不松口,然而,黄鼠狼还是已经濒死了。
爸爸来看时,院子里还弥漫着臭气。也许是被臭屁熏的,也许是因为冷,贝楼不停地打着喷嚏。老爸不假思索地说:贝楼今天起住门斗,给他铺个皮垫子。
老妈没反对,立即取了一个皮垫子铺到鸡窝外面。打着喷嚏的贝楼嗅了嗅皮垫子,死活不过去。老爸是农村长大的,对老妈说:垫子是狗皮的吧?贝楼是土狗不假,却灵得很,狗皮垫子他不会用。
老爸取来自己的狍皮护腿放到鹅圈与鸡窝之间。贝楼嗅了嗅,满意地趴了上去。似乎还觉得不过瘾,直接钻进护腿的腿洞中。

1976年5月,贝楼再立一功,这一次更加神奇。
5月的一天,放学回家贝楼却没来迎接我。去草地一找,发现草地上贝楼“放牧”的三只大鹅也不见了。
家属院中间有片足球场大小的草地,夏天各家的大鹅都散放在那里。我也带着贝楼在这里放鹅,头上是白云在蓝天里游,脚下是白鹅在绿草中走,要多惬意有多惬意。更惬意的是贝楼已经能作许多事情,比弟弟都有用,俨然家里的“小大人儿”。
早上,贝楼背着给妹妹换奶的奶瓶,蹭我裤脚催我上学。到了大院门口,他边摇着小尾巴目送我远去,边等待送羊奶的农民到来。贝楼从不跨出大院门一步,因为我不许他出大院门,我怕他跑到医院去,他的妈妈和兄弟们还在,我怕他去了之后再不回来。大院门卫也知道我这个心思,也不允许贝楼出大院一步。
换到奶后,贝楼一路小跑回家卸下奶瓶,就跑到草地上,看守我家的三只白鹅公主。中午放学之前,白鹅公主们的安全、肥美草场的选择等一应事物都是贝楼照管,从来没有差错。

本图片来自网络
大院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贝楼和大鹅,他们到底哪里去了?
见我着急,姥姥就宽慰我:不怕的,狗都认家,不得走丢。姥姥是专门从哈尔滨过来帮妈妈带弟弟、妹妹的。
弟弟却说:鹅有翅膀会飞,飞到天上玩去了,贝楼也追到天上,贝楼没翅膀,就下不来了……
姥姥呵斥弟弟:年个孩子,也个贝楼都比你聪明;姥姥是山东掖县人,说一口掖县话。
晚上九点,院里的大喇叭都停播了,贝楼仍没有音讯。夜里十点,弟弟忽然说听到贝楼的叫声。这一次他没错,因为我也听到了!
哥俩光不出溜地下了床,一头扎到乌曲麻黑的院子里。开门声惊动了老爸,他也跟了出来,也听到了贝楼的叫声由远而近传来!
我和父亲连忙把院门打开,我高声呼喊贝楼的名字,贝楼显然是听到了我呼唤,远远“汪汪”两声算是回应,却不像平时那样飞一般冲过来,远远地似乎在兜着圈子驱赶着什么。
黑暗中我和父亲都听到了贝楼的低吼中夹杂着鹅叫,老爹脸上全是笑,兴奋地说:我说咱家贝楼有灵性吧,这家伙把鹅找回来了。
果然,三只大白鹅一拽一拽从黑暗里拽了出来,一进门斗就挤到鹅圈前抢着吃食。但是,贝楼还没回来,听他的叫声,似乎还再追赶恐吓着什么。此时,老爸也是一脸懵,莫名其妙地盯视这黑黑的夜。
终于,贝楼从黑暗中钻了出来,他的前面是一只被他驱赶着的花鹅。花鹅是个帅哥,不是家属院的,居然被贝楼抓俘虏一样押了回来!

本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午饭时,老爸总结了案发经过,用现在的话复述就是这样的:家属院后面的铁丝网有个缺口,缺口上挂着鹅毛。显然,白鹅公主们趁着贝楼去换奶的机会,从这里溜出了家属院。他们溜出家属院的起因是帅哥花鹅,至于是花鹅勾引了公主,还是公主对花鹅起意,不得而知,反正在鹅们卿卿我我的时候,贝楼一路追来。可是三位公主和帅哥正是你侬我侬,咋地也押不回来,贝楼索性就把花鹅给俘虏了,折腾到小半夜,终于押了回来……
姥姥说:年呢,也个可是养了个狗?也个是养了个小神仙呀!
谁也想不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贝楼最后的神奇,也是我和我的贝楼最后的欢乐时光。
我把贝楼丢了,贝楼应该一直在寻找我的路上奔跑,我总这样想
1976年,中国巨变开始。也是这一年,我把贝楼丢了。
10月,“四人帮”粉碎没几天,老爸接到立即去驻绥化某部队报到的命令。之后没几天,老妈也接到命令,军分区以最快的速度将她和父亲调到了一起,这在以前可是没有过的事情。
事情太突然,绥化那面还没有腾出房子,爸妈都要暂时住宿舍。我和弟弟、妹妹就只能去哈尔滨的姥姥家。哈尔滨不许养狗、养鸡鸭,于是,贝楼连同四只大鹅只好暂时留在北安。
北安的房子留给了姚叔叔,姚叔叔是部队的械理员,人很好,很憨厚。暂时留下的还有家里可怜的私人物品,比如一架蝴蝶牌缝纫机。妈妈叮嘱姚叔叔,等绥化有了属于我们的房子,再麻烦他把这些东西送过去。
在姥姥家,总会在梦中见到贝楼追着我送别的情景——离开北安的那天,贝楼追到了家属院门口,破天荒地冲着我们的吉普车叫。以前他送我上学从来都不叫,只是摇着尾巴看着我走远。这天贝楼一反常态,不仅吠叫而且不顾门卫的阻拦冲出大门,跟着吉普车扬起的烟尘追了好远好远……

本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候,我九岁,只记得梦中的烟尘好高好高,贝楼就在烟尘里一直跑呀跑。
1977年1月,我和弟弟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我还不到十岁。
本以为到家就能见到贝楼,然而却没有。爸爸说姚叔叔忙,过一阵就会把贝楼和家具带过来。我总在想,贝楼是不是长大了?贝楼是不是更聪明了?贝楼一定是更聪明了,因为跟我一起到绥化的弟弟,留在姥姥家的妹妹,都已经聪明了很多很多。
5月,满十岁后的第四天,姚叔叔带着一辆解放车来了。车里装着四只大鹅,装着妈妈的缝纫机和几口箱子,就是没有我的贝楼。大鹅们似乎没有变化,缝纫机和箱子上却有烟熏的痕迹。
我追着姚叔叔问:贝楼呢?怎么不见贝楼?
姚叔叔从驾驶楼里抱出一只小狼狗,一脸惭愧地对我说:贝楼丢了,找不到了,这是叔叔给你找的小狼狗,真正的军犬……
我发疯一样摇着姚叔叔的胳膊叫喊:我不要你的破狗!我的贝楼怎么会丢呢?那么聪明的贝楼怎么会丢呢?!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故事,一个让我伤心至今的故事——

图片来自网络
姚叔叔一家住进我家后,起初贝楼冲着他一家老小叫个不停。后来他见大鹅们和家里的家具都在,就不再叫了。
每天中午,贝楼还是去家属院门口等我,直到傍晚才跑回家里,反复地嗅一遍我们用过的家具后,静静趴到狍皮垫子上,侧耳听着门外的动静,每当有人经过,他就竖起耳朵……
天冷了,姚叔叔怕贝楼冻着,想让他挪到屋里去睡,就拿走了贝楼的狍皮垫子在屋里给贝楼安排了新位置。贝楼叫了两声,又把垫子叼回来,坚定地守在鹅圈前父亲给他指定的位置上。
又过了几天,姚叔叔的母亲作午饭时不慎引燃了柴堆,一把大火呼呼啦啦地烧了起来。正是中午时分,家属院里男人不多,大火越烧越旺,等到大家赶来把火扑灭,房子烧塌架了。
救火的时候,贝楼一直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火灭了房塌了,贝楼却谁叫也不走,一直站在火场前吠叫,贝楼是轻易不叫的。
第二天,姚叔叔去找贝楼,见他还趴在原来门斗的位置上,此时门斗已经没了,只有一片冰凉的瓦砾。看到姚叔叔走来,贝楼的两只前爪压住了一小片东西,戒备地望着他。姚叔叔定睛一看,见是烧得只剩下一小片的狍皮。
第三天,姚叔叔又去火场,想把贝楼带回临时的家。远远地看到他走来,贝楼站起身低低地哀嚎一声,叼起狍皮转身向家属院的后院跑去。
姚叔叔见昨天带来的食物贝楼一口没动,又见他叼着狍皮跑向后院,以为他一定不会走远。没想到,贝楼从此再也没回来。姚叔叔说,门岗没看见贝楼出家属院,家属院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351已经在几个月前搬离了北安,贝楼不可能去连我都不知道的地方找妈妈。

图片来自网络
我问姚叔叔:贝楼的饭盆呢?
姚叔叔一脸惭愧的说:救火时人多手杂,饭盆实在是找不到了……
我知道贝楼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世界上属于贝楼的东西只有四样——家、家里的我、父亲给他的狍皮、我给他的饭盆。饭盆就是在医院给贝楼喂羊奶的那个,那时贝楼才两个月,我不满7岁。
房子塌了,家没了。我不在了,饭盆没了,他的妈妈和兄弟也找不知道在哪里。
贝楼叼着仅存的一小片狍皮跑向后院,他一定是钻过了缺口,他俘虏花鹅回家的缺口……但是,他能去哪儿呢?贝楼再也不会回来了!

图片来自网络
执念,关于执念的那些事,因为执念给比格犬起了名字
我粗暴地拒绝了姚叔叔的小狼狗,姚叔叔一脸惭愧地带着小狼狗回了北安。姚叔叔走后,老爸赏了我两记耳光,惩戒我的失礼。我却梗着脖子说:打我,打我贝楼也回不来,打死我算了!
本来以为接下来老爸会用他带铜扣的皮带招呼我的臀部,我不在乎,就是想哭,想痛痛快快声嘶力竭地哭。
老爸却没打我,只是叹了一声对我说:你想没想过,贝楼没准现在正在找你的路上,你要坚信他一定会找到你,要有执念……
我不懂啥叫执念,却哭了,满十岁的第四天,哭得昏天黑地……

执念一:
从那天起,我就期待着贝楼会突然钻出来站到我面前,也许是在放学的路上,也许是在新家的门前,也许是在四只大鹅悠闲吃草的时候……尽管期待没有变成现实,但还是期待着。期待中走完了童年、少年、青年……一路走成一个啰啰嗦嗦的小老头。
九十年代末,我首次上网,网名是“十岁”,头像是一只叼着雪茄的大狗。周围的同事以为我是搞怪,他们不知道,从十岁那年起,我就一直在等待一位朋友归来。二十多年了,没有一只狗狗可以活二十年……但是,贝楼是一条狗狗吗?他是精灵,他能够创造一切奇迹。这就是执念。

执念二:
几个月前大院的孩子聚会,一个老哥哥对几个年龄稍小的伙伴说:可别看柯湘(我的外号)现在跟个文化人似的,你们谁敢动他妹妹一手指头试试,板砖菜刀钢叉军刺……啥顺手就用啥招呼你,不打出血来也得打出屎来;你们看看,我后脑勺上的疤,就是这小子一板砖拍的,这小子十一岁就敢拍我这十六的,一下子就把我拍医院去了,脑震荡……因为啥?就因为我骑车刮他妹妹一下……
几个小兄弟一叠声说:柯湘哥威武,十一岁的敢拍十六岁的,威武!这要是没有血肉真情做不到呀……
他们不知道,我的记忆里中一直烙印着贝楼跑跑颠颠为妹妹取羊奶的画面。从小喜欢喝羊奶的贝楼,闻得出瓶子中羊奶的味道,他却一口都不偷喝。贝楼精心照顾的妹妹,我有什么道理不呵护呢?别说对手是十六的,就是二十六、三十六,我也照拍不误。
这就是执念!

执念三:
老了,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拒绝,就象无法拒绝肿瘤一样,我也不能拒绝比格犬的到来。终于打破了自己不再养狗,也不许家人养狗的执念。却也悄悄地将一些执念继续着。
也就是一个月的功夫,小比格已经可以认家了,只要抖三下狗绳,对它说“领姥爷回家”,它就会穿过楼群里,准准地把我带到家门前。不过它轻易不会奔向单元门,而是咬住狗绳赖赖地要求再玩一会。
也就是一个月的功夫,小比格已经认识红绿灯了,以前我一直恍惚地记得狗狗的眼睛是不能分辨红绿的,但是小比格居然就能!我还是觉得它是靠观察周围的行人得出的结论,只要其他行人开始横穿马路,它立刻就衔起狗绳前端,牵引着我小跑着过马路。时不时还回头看,似乎在招呼我:过马路,跑步!

我家的小比格
小比格是个小笨蛋。回家的头一天,它充分显示了猎犬的本色,鼻子就没离开过地面,嘴巴也不停地咀嚼着什么。夜晚,小比格忽然从尿垫上咧咧巴巴踅摸到卧室,后腿似乎伸不直了,嘴里不停地哀叫。仔细一看,小家伙的屁股上居然挂着一小节便便!原来它刚刚吞下了一根头发,头发连住了便便,它怎么也夹不断……于是,我就昵称它是“傻狗”。
小比格还是个小无赖。只要遇到女性,只要人家乐意爱抚它,不管是老是少,小比格都惬意地接受,甚至原地打滚亮出肚皮任人家抚摸。小比格就这样撒娇卖萌,从来不咬外人。然而,却总是偷偷咬我妻子,本来妻子正在给它喂食,它也吃得好好的,却忽然回头在妻子的脚上咬一口,然后就跟啥也没发生一样,闷头吃食。如果妻子呵斥它,它就哼哼唧唧耍赖,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却不耽误吃狗粮。
一来二去,妻子怒了,她说:唉唉唉,你是“傻狗”还是白眼狼?搞搞清楚,是我抱你回家的,你怎么对别人那么亲,却专门咬我呢?
是时候还多年的债了,那是我欠贝楼的,欠了贝楼一生,于是对妻子说:
你要不抱它回来,可能现在它还在妈妈怀里吃奶呢,为这个咬你不冤吧?它为啥对别的女人那么亲?那是它以为见到妈妈。所有的女人里,只有你是夺走它妈妈的人,不咬你咬谁?
妻子愣了一会儿,问我: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简单啊,把它送回到它妈妈身边去,就没这事儿了。
妻子半晌不语,忽然明白过来,嚷到:你这是编故事,差点把我骗了,你是不是当我也是“傻狗”呀?少废话,吃药,吃完药给我遛狗去,现在小狗没有亲妈了,只有姥姥。傻狗是姥姥的,姥爷是负责遛狗的,编故事也没用!
临出门时,媳妇又说:母子分离是挺残忍,送它回去见见它妈妈也行。不过你得给狗起个名字,如果咱们叫它“傻狗”,它妈妈听了也会咬人……

我家的小比格,名字叫做张豆花
感谢妻子,压在我心里的一个债可以还上了。欠了贝楼的债,也是执念。
我说:看见女性就撒欢儿,这小东西就叫逗花吧,见到“花”就逗的意思。
领着比格走了没有两条街,妻子的微信来了:不叫逗花,叫豆花,别以为我是“傻狗”,猜不透你打的什么坏主意,少“逗”我!
我笑了。生活方式,我选择平实直白;爱的表达,我选择含蓄,
这也是执念,从童年烙印出的执念。
童年结束在吉普车扬起的尘烟里,尘烟渐渐淹没了我精灵般伙伴的身影。
童年一直没有结束,因为伙伴一直在尘烟里追赶我,精灵一般追赶着我!

写在后面:这么啰嗦,自己看完都累得眼睛酸酸的。作个保证:如果我把豆花丢下了,像丢下贝楼那样,将不再写一个字。所以,我不会丢下它。也许做不到,但会尽力。明白我的意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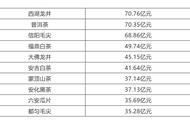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