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陵河的鱼群:生态宝藏

小时候,严陵河里的鱼真多!
清澈见底的河水,成群的鱼游来游去,悠哉悠哉。有细长的白条,大嘴的马口,金黄的鲫鱼,红尾的鲤鱼,胡须长长的鲶鱼......还有一种小嘴,红眼,扁身,披着一身五彩外衣的,小朋友们叫石光皮,现在知道,叫四光皮,书名叫鳑鲏。它们在水草丛中,在阳光下闪着斑斓的光。我们总是捉一些,放在家里的水缸里当成金鱼养......我们经常站在岸边,静静地看这些鱼在水里表演,有的鱼会精神抖擞地“哗”一声跃出水面,来个精彩的翻滚,然后优雅地钻入水中,荡起层层涟漪。
我好奇地问父亲:“咋这么多鱼?”
“千年草籽,万年鱼籽。有水就有鱼。”父亲说。
我们在水边的沙滩上,开条水沟,在水沟的下面放个竹编的簸箕。一会儿,成群的鱼就大摇大摆,你推我挤,噼噼啪啪地钻入我们的“布袋阵”。我们赶紧跑过去堵住进口,就沟内捉鱼了。折几根柳枝,捋去叶子,把鱼从鳃中穿过,拎着几串鱼高高兴兴地回家。
有一年,四叔从县城拿回一个粘网。我们把渔网往河对岸拉,网一下水,这边就粘住了鱼。等到渔网拦住河道,上面已密匝匝一层鱼,把网也坠入了水中。我们只好把网拎到岸上摘鱼,一网摘了一桶。
那时候,砍根竹竿,绑根麻线,弯根衣针,挂上蚯蚓,就上鱼了。白条不顾头青脸肿,疯抢一气。鲫鱼吃口像温柔的姑娘,慢慢地品尝。鲶鱼凶猛,一口吞下,扭头就跑。黄刺公一出水,一边“哥呀哥呀”的求情,一边抖着身上的刺,向人示威。它吃食轻狂,总是把钩吞入肚中,很难取钩,一不小心,就被它身上的刺扎住,殷红的血就流出来,焦疼焦疼,疼得龇牙咧嘴,跺脚甩手,赶紧热尿一浇,疼痛顿消。但它刺少且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烩一锅,很是解馋。现在,大城市的超市有卖,二三十元一斤,但不过是饲养的罢了,营养味道与野生的不能相提并论。
夏天在河里洗澡,鱼也不认生,成群的围着啃你:拱你脚,咬你胳肢窝,钻入下巴颏。痒酥酥,麻飒飒,你躺在水中的沙石上,美得闭上眼,不知不觉进入梦乡。现在,一些地方开发了鱼按摩消费项目。一问:“嗨!我们小时候经常让鱼按摩,有啥希罕!”
隔着水,能看到一拃长的沙轱辘,身子钻在沙中,只露出灰灰的花花的长头,你慢慢走过去,两手合拢,轻轻一扣,一条沙轱辘就在你手中扭动了。有时,你感觉脚下一软,伸手下去,就能拉出一只王八来。一煮,全家嫌腥,乌鳖杂肉,谁也不吃,只好倒了。谁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野生的王八现在这样金贵。那时,真有点暴殄天物!
那时候,雨水多,严陵河每年都要涨大水。大水过后,岸边的沙坑,总能给我们留下不少的惊喜。有一年秋天,村民在西河的沙坑里发现了一条鱼,小碗口大的嘴,在水面一张一合,后来人们打捞上来,一称,八十多斤,引起不小的轰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那饥饿的岁月,在我的童年和少年,严陵河不仅带给我们快乐,也满足着我们的胃口,给我们提供着营养。
小时候,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上午第四节课,肚子叫,头发晕,眼冒光。一放学,先到河里逮几条鱼,泥一糊,火一烧,就狼吞虎咽吃起来,几条鱼下肚,人就有了精神。再拎上一串,回家放窝灶里烧。谁家舍得油炸呢?案上那点油,来客了用根筷子蘸了拌菜用的。
经常听父亲谈起“三年自然灾害”:草吃光了,树皮啃完了。谁谁饿死了,谁谁全身浮肿了......
我总是奇怪地接话:“咋不捞鱼吃?”
“河水都叫人们筛过了,哪还有鱼?你别说,河里的鱼,确实救过大伙的命。”父亲接着说,“谁想,过两年河里鱼又多了起来!”
十年前,我拿起钓竿,来到严陵河边,钩子刚入水,就黑标。一抬,力道不小,拉上来,二斤多一条鲶鱼。一会儿,钓了五六条,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五年前,严陵河断流了。荒草覆盖,垃圾堆岸,鱼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年夏天回家,严陵河有水了。浅浅的,清清地河水汩汩地流着,成群的小鱼在水草间玩耍。心想:“再过两三年,这些鱼能长二三两吧,到时河里一定充满了生机。”孩子说:“我要回来钓鱼!”可到了冬天,严陵河又干涸了,鱼又消失了。
这几年,严陵河一直没水,当然也没鱼,只有没腰的荒草和阵阵恶臭。回家钓鱼成了奢望。
十几年钓龄,装备越来越良,技术越来越高,饵料越来越好,可钓点却越来越远,水质却越来越差,渔获却越来越少......总让我念念不忘,小时候的严陵河,不忘严陵河里的鱼。
“千年草籽,万年鱼籽。”严陵河里的鱼籽在等待化籽成鱼,传承着鱼族不灭的神话!许多河流和坑塘的鱼籽也都在做着化籽成鱼的梦:潮平岸阔,逆流跃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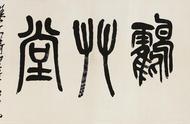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59号